

李晁:在《月球》里又见鲍时进,真有别面之感,他像根针一样扎在小说里,牵引着刘丽丽。你是怎么想到还让这个人物出场的,在《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里,以鲍时进为代表的人物,见证了大厂时代的兴衰,那种氛围的呈现属于一个大问题,我们先从他来谈谈《月球》。
郭爽:鲍时进是我写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人物。这么说不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偏溺,而是我发现,他从诞生之后就没有消失。我自己偶尔会想起他,朋友、读者会跟我说起他。他和他连带着的那个世界庞大又生猛,给我们许多提示。写《月球》的时候,最开始的萌发是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中年女性在看电视,电视里的主播是她丈夫的情人。电视很大,睫毛都数得清,她也就一点点看见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这么一个意象后,我突然想起了刘丽丽,这个在《鲍时进》里只寥寥出现过几笔,但很有意思的人物。于是在《月球》里,刘丽丽成了主角,那个世界一如既往在丰沛、盛大又沉默地运转,许多面孔闪回,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和未来时。你是《鲍时进》最早的读者之一,后来又在《山花》编发了它,我也很好奇,你看到《月球》这么一篇小说会是什么感受。
李晁:我阅读你的小说恰好有一个感受,正是对时空的呈现,譬如《鲍时进》,在场感非常强,既有时代赋予小说的大背景,又有这一背景之下的纤细触感,小到一道菜,都很有声色,这声色不是单一的,它有着与人物共同的呼吸乃至秉性。具体到《月球》,似乎也是这样,有着基于现实又超于现实的视野,当然“月球”的隐喻是一个实在的出口,它的作用把小说从一种实际困境里牵引出来,隔了一些距离,这让读者舒一口气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类无法摆脱的现实际遇与远古基因里对未知事物的张望、想象,我觉得这带来了心理平衡,即人是渺小的,受限于生命与生命进程里的琐碎(通常来说是苦与难),可同时人类又是阔大的,在面对未知的想象力方面,人又与宇宙同在,表现出一种超拔感,这两者的同时呈现,你是怎么想的?
郭爽:现实与超现实,远古/未来与当代,苦难与超拔,这些在小说里共生、对等的意念具体是以一对母子来承托的,也就是刘丽丽和儿子,也可说是刘丽丽们和儿子们。与《鲍时进》相比,当下的世界依然精微、生动,但交织作用于“当下”的,不再只是历史。反思也不只是历史。如你所说,人的渺小、生存的苦难,这些东西往往是受限于生命进程的,但我们又都知道,生命进程有前史与未来。在人作为个体诞生于世界,完成与社会身份、肉体、精神等共生的进程之前和之后,还有很多很多事发生、作用于每一个人。宗教、哲学、科学都可分析人作为人的一生,但对于作者来说,更想探究其中神秘、幽微、暧昧但充满生之激情的部分。《月球》就是一次不满足于现实,继而更放任地想象的过程,也是问询自由究竟何来、何为的过程。
李晁:说到肉体,我还在意这篇小说里处理到的问题,就是身体本身,以我的阅读经历来看,似乎对身体疼痛、病态的呈现已经陌生了,不知道小说家们是否对身体带来的人的状态有所忽视,我读到的更多是“健康人”所面临的问题,社会带来的种种缠绕等等,都根植于事件,而极少看到落在人物身上的病与痛那么实在地影响到了一个人。《月球》里的儿子自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又没有从他的角度来感受,感受这一切的还是“母亲”刘丽丽,包括她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衰老带来的双重压力,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博弈,又是小说的一个有力点,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
郭爽:对,既然主角是一个中年女性,叙述视角也以她来展开,那为什么添一个生病的儿子?如果是问询自由,为何不设定为一个全然活泼、就是“未来”本身的儿子来“拯救”这种困境?我本质上不相信任何形态的达尔文主义,但也不信奉简单的循环论、周而复始。人的生命形态是多维的,年老的亦有年老的活力,年轻的也有年轻的衰微。但聚焦于身体上,或者把人集中于身体、精神双重丝毫不可分割的存在,是我越来越强地感受到了肉体存在对于人之为人的提示。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可存在于芯片中,可继续交谈,但我想,是跟我们此刻、之前的谈话所不同的。尤其是当人与人面对面,直接面对一个承载了对方精神的肉体时,肉体就不是驱壳而已。它是我们的起点,也是边界。身体的存在神秘,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联也是。所以儿子的病是实在的,也是一种反思,因为不能自如行动,他是精神大于身体的存在了。而母亲刘丽丽,则还是“有血气”的人,她不能像儿子那般超脱。小说中写到儿子拒绝手术,因为“不想成为不完整的人”,也是一种多重意义的反抗。
前面你说到“人与宇宙同在”,是的,从另一角度来说,宇宙因人意识到宇宙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人与宇宙同在。
李晁:提到这个“儿子”形象,小说其实避免了提到死亡,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未来在小说里悬而未决。“儿子”的状态有一种迷人之处,就是你说到的“不想成为不完整的人”,不论他玩游戏还是把视角对焦到了宇宙空间,对准了迷之存在的月球,可以真切感受到这个人的“非人”状态,几乎是以一个天真的哲学家的面貌而存在,因为世俗生活对他已拒之门外,那么这一段人生经历被直接跳跃之后,一个人难免会对“存在”本身有所聚焦,但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家庭这一仅仅存在的世俗影响,譬如对父母,对小说里的第三者宋霖乃至鲍时进都有独到的观察与理解,甚至小说里一个小小细节打动人心:“她正要转身离开时,儿子拉住了她围裙的后摆。她突然想打开儿子的手,恐惧于儿子已经识穿了她。可这是件从袖子到正身连成一片的大围裙服,裙摆被攥住了,整个身体就被牵引住了。”我觉得小说写到这里,一种浓重的哀愁被轻描淡写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在母子俩体内纠缠,这变化之间,正是小说的丰富所指,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无限接近与不可接近?
郭爽:对健全人来说,死亡与日常是平行的,轻易不会想起、去想。但对于病人和有病人的家庭而言,死亡就带有了紧迫感,无论病重还是轻。像小说里的儿子,是个慢性病患者,家里有钱,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死亡确实早早对他彰显了终点的存在。打牌时,如果你早早就知道了底牌,那么出牌的顺序、方式和整个牌局的心理,都会不一样。可能轻松了,可能会恶作剧一下。甚至对于日常与伦理,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与对待。他站在终点看。母亲与父亲、父亲的情人,包括鲍时进,这些人本应有简单、确定的伦理判断,对他来说则有别的意味和方式。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
母亲则活在当下。她的忧愁、愤懑或者隐秘的快乐,都是实感的。虽然她是个知识分子,但知识、经验和情感、伦理给她带来重重束缚。她无力挣脱,几乎是在顺着命运缓缓下坠。
你提到的这一细节,是母子之间儿子主导的互动,儿子攥住母亲裙摆,只是攥住,却对母亲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他们的相关、相连,具化在一个简单的动作中。让母体这个诞生相连关系的主体想要逃离的愿望无法再掩盖。她想要走,儿子抓住了她。该怎么办?
这就是你说的“无限接近与不可接近”的一瞬吧。于是在小说后半段,有这么一个相连的动作后,两人的个体更清晰地运转,他们必须各自运转。
李晁:没错,结尾时,“儿子”的体验一下毕现,在日记里,“母亲”消失、吐奶嘴的意图,都让人印象深刻,是对这关系的最终回响,其实也暗合了其后的人生路线。回到“母亲”这一角色,刘丽丽,这么一个大厂里生长并工作后离开的人,若不是“儿子”的状况,她该是一个被人“羡慕”的人物,通过小说的人物关系网络,我们很能感受这么一个女人的变化,她与丈夫,与鲍时进,与弟弟,与第三者,与闺蜜们的接触都只露出一丝痕迹,这里那里,但读者确实可以凭借这丝丝的痕迹组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不同状态下,女人的心态值得玩味,她的理性压制了一手好牌逐渐带来的捉襟见肘,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人生之感丰富而可信,更难得的是你没有施加一种显在的哀怨,而是用一种冷静笔触去处理这么一个人,这是以理解为前提的写作,你怎么看待她?
郭爽:今年是杨德昌《一一》首映二十周年,我看到不少纪念文章。其中有人模仿《一一》里的小男孩洋洋,拍下了很多人的“背面”,“你们看不到的,我拍给你们看”。我想人确实是看不到自己的“背面”的,因看不到而容易耽溺,自恋、自怜也多因此而生。刘丽丽的人生,对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已有种种可羡慕之处了。离开了大厂,读了大学,成为知识女性,包括最初的婚姻和未生病前的儿子等等。但这只是一面,是证件照般拍下的正面。她人生中的不幸,如果我们把被丈夫屡次背叛、家庭破裂、儿子生病、辞职在家做全职主妇这些都姑且看作不幸的话,其实并不是某一刻突然到来的,而是跟她的前半生密切相连,一次次的选择后她一步步走到了这里。这是旁人看不到的“背面”。可我对刘丽丽有一种期许,期许她能看到自己的背面,也许就从这个有月亮的夜晚开始,从跟儿子这一通谈话开始,从化身一只游戏里的仓鼠、摆脱刘丽丽本身开始。包括她跟老鲍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复杂的,但我希望他们在经历更多的时间后,能指向爱。爱让我们超脱。
从天文的角度来说,月球背面是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一面,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环绕月球,不然看不到背面。月球背面更古老,直接接收太阳光,不接受地球反射的太阳光,来自地球的电波干扰也会被遮蔽。我应该把这个加到小说里去嘿嘿。
还有这么一段资料:
天文学家一直希望找到一片完全宁静的地区,监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电磁信号。而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因为月球自身屏蔽了来自地球的各种无线电干扰信号。到月球背面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是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科学家或将窥见大爆炸后宇宙如何摆脱黑暗,点亮第一代恒星从而迎来“黎明时代”的信息。
好玩吧?寻找黎明时代的信息。
李晁:小说里写过一句,“你看到月亮,我也看到月亮,但我觉得,我们在地球、不在月球,算不得真正的家。”读到这里难免目光一停,这句话是“儿子”对时空的观察,充满了一种寄托,也似乎回应了你说的“背面”问题,事物的“背面”确实很难被注意到,小说的一个功能恰恰正是如此,她就得提供往常不大注意、被忽略掉的“风景”,这风景可能来自我们熟悉的环境,也可能来自更陌生的事物,小说里的人物即是前者,而月球恰是后者的化身。这么看,人类的繁衍和宇宙爆发似有相同之处,幼儿的诞生,就是新星的诞生,“它”本身是一个新的空间,会挤占和吞噬其他空间的存在,而家庭是“它”的制造者,某种程度上更为“它”所改变,如果“它”能量够大,会带来种种吞噬,从而造成别的星球导向自身从而自身坍塌或者逐渐远离,我不知道这像不像黑洞?但从这个角度讲,“儿子”恰巧是这样的存在,我们借此可以反观家庭人物的变化,好玩的是,小说里的“儿子”似乎半明半暗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存在。
郭爽:是黑洞,也是风暴眼。我喜欢最后儿子的那段日记。与母亲对话时不同,这里面的语气属于私密的他自己,也有非冲突式的、暗涌的情感温度。也许某天,儿子的故事会延续、独立,我希望那是新的风景。
李晁:你说希望经历更多时间之后,刘丽丽与鲍时进的关系会指向爱,这正是小说留下的模糊印象,比如鲍时进见到刘丽丽的儿子让喊“爸爸”,这一幕有一种天然的真切乃至亲切感,这是一个大环境出来的人所拥有的他人不可具备的“亲昵”,此种关系在当下环境里已经稀缺。鲍时进这个人物在当年的环境里是引人注目的,我对这样的人物不陌生,很容易从儿时置身的人群中分辨出来,所以我读他与刘丽丽的这一幕就想到了一种关系,超离于既有家庭和社会规范的存在,俩人不一定要发生什么,但那种磁场效应煞是迷人,它是以熟悉为背景的,在这熟悉之中容纳了一种彼此理解和似有若无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寄托吧,最后看理解是更大的爱。
郭爽:我也很喜欢他们之间远超过简单的男女感情的这些微妙细节。写到这部分的时候,脑海里的色调确实是不同的。有阵子我反思自己对1990年代的喜爱甚至沉醉,是不是怀旧情绪的衍生。那是我们的成长年代,人和人的关系,人周围的环境,说话的方式和服装家具的色调都跟现在不同,也有别于更多被提及的1980年代。很多事情在记忆里成为风景本身,不需要修饰,也让长大后的我领悟到那个慢调子的生活里流过去了太多珍贵的人和事。到1990年代的后半段,就是带着热望与信心冲向新世纪。我很清楚地记得跟同学一起去看《泰坦尼克号》的夜晚,也记得2000年1月1日去邮局买明信片盖纪念戳……话语方式不同了。之后就开始加速度,有点像被塞进了高速转动的离心器,很多事还没开始等待就已经过去了。
人和人之间由于时代印记带来的特殊磁场,部分延续,部分消散。但对于经历过的人,却能在日后的蛛丝马迹中辨认出这种不复存在的珍贵情谊。对,是情谊。
鲍时进和刘丽丽曾是恋人,但如果说情感教育是持续一生的教育的话,我希望他们之间有可能翻越世俗的定义,有能力去爱,学习爱,懂得爱。
李晁:确实是情谊,单纯而又抱有希冀。说到九十年代,按我理解,“80后”才是真正的九十年代的孩子,能想起很多那年代的感觉,譬如人的精神面貌,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姿态,在慢调的生活中有种种可堪回味之处,远没有如今的快速与人面目上的改变,那时尚没有如此多戾气,还有空间让人与人享受朴素的交往,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紧密,那是直接面对面的关系,而不似如今大多隐埋在科技带来的“便捷”里,没有被众多符号被如此多的信息所挤占,更容易心猿意马、浮躁不安。“怀旧情绪”,并不坏,因它还没有远古到我们触摸不到,恰恰这是这一代人的清晰来路,所以我觉得不必有一种包袱,面对过去和面对当下以及面对未来,同样重要。在当下,似乎写科幻、写反应当下热闹话题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但题材实在没有高下,如果有,那讲述这一行为就要受到质疑。我在意还在于,怎么去讲,人类生活的变化需要怎样的呈现?这时候,回望就更加需要勇气,所以期待你后面的作品。
郭爽: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段话让我很感动。也不只是感动,就还有点难过。想起春节时在家看老照片,有幼儿园时代的,小朋友都穿得鼓鼓囊囊,戴着围兜、袖套,胸口别针别着一条手帕。想到现在时不时就有砍杀幼儿园孩子的新闻,就很心痛。什么改变了?什么不可以被改变?哪些成功是值得称许的?哪些成功是可鄙的?如果说在写过去的年代时我会感到痛苦,就是因为有这些潜意识在比对的时刻。而我能做的,只是让鲍时进这样的人不要消失,不像很多人和事物一样被消失掉。而像刘丽丽这样本来在一篇小说里滑过去的人,也可以重新讲述、获得新生。
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
李晁:对,“重新讲述,获得新生”,因为这是来自“我”所见,我存在,我纪录,这是作家面对世界的路径,不要让那些人事溜掉。我之前才编了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新长篇《流俗地》,恰也回应了我们所谈的话题,她的创作谈标题是《吾若不写,无人能写》,让我感同身受。就是这里面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作为,以旧有人事为依托,不断处理新问题,这是我读你小说的一个感受,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到从现实来到现实去的作品,是这样一种层面,而《月球》的出现,又往前走了一步,它的切口很小,环境人物关系是扎实的,但她眺望的方向又摆脱了她所依托的氛围,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是否也是你小说观变化的一个例子?
郭爽:《月球》是小的,小到主体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晚上,发生在室内,只有母与子两个人。这么说会联想到戏剧的处理方式,角色在舞台上通过对话来推进和达成动作、冲突,进而完成整体的叙事。但《月球》又是不止于此的。刘丽丽作为主体叙事视角,她的意识流冲破了房间,冲破了时间,在更绵长更广阔的时空里巡礼。是的,是巡礼。在这种不断地蒙太奇跳接中,构成刘丽丽这个人的记忆、经验和尚未定型、尚未有答案的人与事一一浮现,像你说的,让人松了口气。另外,月球作为小说里现实世界的“实景”,也作为隐喻出现,更作为一个母与子通过游戏这个虚拟场景可登陆的“他方”存在。这也许就是最开始你谈到这篇小说有很强的时空感受的缘由?
如果是一年前的我来写这个小说,不会有这么多层次的时空交叠,也不会把主题场景限定为这么小、时间限定得这么短。这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写作难度。你说写作要不断处理新问题,我很认同,这个新问题其实不是题材层面的,而是小说作为媒介之一种,如何应对日常中其他媒介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经验感知、讲述方式的变革。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视频、综艺或者电影,多半要同时看视频流(高频剪辑),还要看字幕、看弹幕,综艺的话还有叠层的后期效果。我们的眼睛和大脑已经被训练成可以同时接收这样的信息流而没有障碍。而如今电影的叙事语法和剪辑手法,也是上世纪电影所不能想象的。相对应的,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也处于这种变革中,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必须更积极地想办法:小说的独特性,用语言来叙事的媒介有哪些不可替代之处?我作为读者,也非常期待能出现新的小说语言,能给我们全新的认知方式。它不一定是关涉整体性的,因为在当下,对任何一种媒介而言,要把握整体性都不太可能,像19世纪小说那样复刻社会整体图景的做法在电视、纪录片、智能手机和短视频的发展之后,小说如采取同样方式不再具有有效性,或者说难以与其他更“逼真”的媒介竞争。所以,从小处着手未尝不是一种办法。对“小”的限定,是为了摒除虚妄的大,更切近最大的真实。
这是从外在环境来考虑的,那么文学本身作为叙事手段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观点,值得一思。
在一本叫《良知实验室》的书里,弗雷德里克·莱西特-弗莱克讲了一个观点:文学是特别适合思考道德问题的空间,也是比道德哲学空间复杂得多的空间,因为道德哲学大多建立在抽象案例之上。他以《塔木德》中的寓言为例:两个男人在沙漠中行走,水壶里的水仅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了。他们该怎么办?冒着一起死去的风险分了这壶水,还是牺牲两人中的一个?
弗莱克进而写道:“在现实中……沙漠中的两个人将会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强壮的人和一个弱小的人,一个博学的人和一个无知的人,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从来都只有个体,和他们各自的品质优点、相互关系、决心意志和个人情况。”
但文学可以进行最严格的精简,只保留虚构故事以表达具体的抽象的情景。这是文学的能力。“实际上,同一个范式可以有上千种变体:这些变体正是由文学虚构来处理。与哲学家们为其思考而假设的场景不同,文学虚构是对可能的现实在具体环境中最忠实的反应。”也就是说,每一个读者都必须为自己设置在这种现实中的行为规则。
《月球》有没有达到对一种抽象道德处境的具体、忠实反应?至少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
李晁:我认为效果是明显的,从标题看,实际就已经有所准备或者说暗示,以我对你作品的一点了解,在没有读到内文前,隐约就产生了一种说是暗示也好隐喻也罢,总之,有了一种新鲜感。再读开头这好奇就更深了。在这一种讲述“现实”的氛围里,不知道你要如何把“月球”这种意象性的东西导入,从刘丽丽身上,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方向,那么就剩“儿子”了,因为他的存在,刘丽丽这个母亲也被带入了这样一种视野之中,从而最终合力完成了小说构建。我们来聊最后一个问题,标题的确定是怎样的过程,是先有还是后加,这篇小说还有过其他标题吗?
郭爽:小说改过好几遍,初稿的时候稿子比现在短,只有不到七千字。但月球的多重意象在初稿中已经有了。改第二遍的时候篇名就改成了《月球》,后面的几遍修改主要在母亲刘丽丽的时空巡礼上。最后一次修改删掉了一条刘丽丽方面的线索,但增加了结尾处儿子的日记。增加日记是突然的灵感,加了后我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可以去月球了。就放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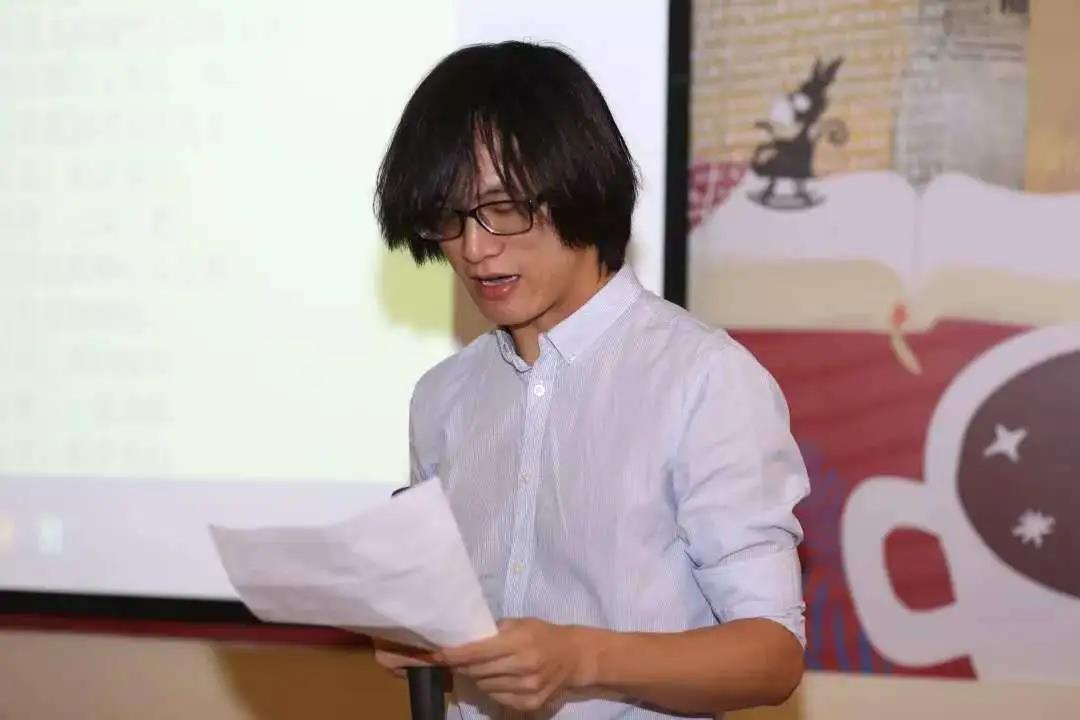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作家、编辑,2007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小说集《步履不停》《超难北》,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等奖项。

郭爽,1984年生,作家。出版《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2019诚品阅读职人大赏·年度最期待作家奖。
相关新闻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